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推动下,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已经正式启动。2020年3月,上海浦东、金山,江苏张家港,山东郯城,深圳南山、宝安等6家基层检察院开启了第一轮试点。2021年3月,北京、上海、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湖南、湖北、广东启动第二轮试点工作。除了采取法律明确规定的酌定不起诉的方式将企业出罪之外,还有的试点单位采用了一种类似于附条件不起诉的方法,即对涉罪企业设置一定期限的合规监管考察期,并对其进行监督指导,帮助其推进合规管理体系建设,期满后验收合格的,不再起诉企业。陈瑞华教授称之为合规考察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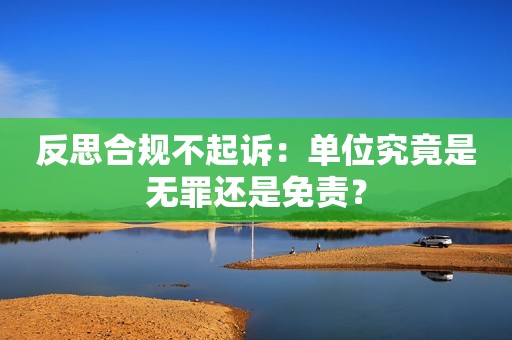
在试点工作开展过程中,许多问题涌现出来,本文想探讨其中的一个问题是,合规考察模式的适用对象究竟是系统性单位犯罪还是非系统性单位犯罪。还将进一步讨论,非系统性单位犯罪是否存在的问题。
有观点认为,根据刑事归责方式的不同,单位犯罪有两种形式:一是系统性单位犯罪,即由单位及其决定或者单位负责人明确授权决定实施的犯罪行为;二是非系统性单位犯罪,即在管理制度缺位的单位中,个人为了单位利益而实施的犯罪且由单位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进而认为,合规考察模式主要应对的是非系统性单位犯罪,因为这样的单位的主观恶性较小,有改造的价值,而那些在单位集体意志下犯罪的单位,恶性较大且难以治理。
对该观点持支持态度的人们举出了实践中的例证:雀巢(中国)有限公司的六名员工为推销雀巢奶粉,通过拉关系、支付好处费等手段,多次从兰州多家医院医务人员手中非法获取十万条新生儿及其家长的公民个人信息,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审理过程中各被告人均辩称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是为完成公司下达的任务,销售奶粉所获得的利润也归公司所有,本案应属于单位犯罪。但兰州中院认为雀巢公司已经通过防范违规行为的合规性文件政策提醒员工依法经营,并对所有员工进行培训,雀巢公司已尽到管理义务,没有失职行为,本案不应构成单位犯罪。因此,该观点的支持者认为,该案中的企业的独立意志,通过合规管理文件得以体现,与行为人(责任人员)的意志实现了分离。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合规制度,那么企业就会因为行为人犯罪而构成单位犯罪,即前面所提到的非系统性单位犯罪。
该观点的支持者还找到了刑法规范中的论据:因为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主要情形正是关联人员利用网络漏洞实施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违法行为,造成违法信息大量传播,或者导致用户信息泄露等严重后果。如果企业没有履行法定的网络安全管理义务,没有建立网络安全管理体系,存在不作为或者失职的情况,并且拒不改正,就成立该失职类犯罪。换言之,只要单位的行为人(责任人)实施了犯罪行为,而单位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合规制度不健全等过失心态或不作为,就会成立单位犯罪,以此论证非系统性单位犯罪的恶性较小。
同时,该观点的支持者列举了域外对于这一问题的部分规定:英国2010年通过的《反贿赂法》规定,只要一个商业组织的关联人员为了获取或保留该组织的业务,或者为了获取或保留该组织的商业优势,而向他人行贿的,就可以直接推定该商业组织构成商业组织预防贿赂失职罪,但能举证已经构建了合规体系的除外。西班牙刑法典第31条第2款规定企业实施有效预防犯罪的合规体系的,对公司内部人员所实施的犯罪行为不承担刑事责任。以此论证非系统性单位犯罪的出罪理由和举证责任。
总结上述观点的内容,就是单位作为独立的责任承担主体,如果没有完善的合规制度,就有可能因内部人员的犯罪行为而承担单位犯罪的责任。公诉机关可以设置考察期限,要求单位在一定期限内完善合规制度,通过验收后就不再起诉单位,而仅起诉单位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但笔者认为,一个企业是否有完善的合规制度,与其是否构成单位犯罪,在实体法层面上并没有什么关联。如果非要说有关联,那也是在证据法层面的关联,而证据法层面的关联,是不可能通过案发后构建合规体系的方式进行变更的。一个犯交通肇事罪的人,不会因为重新考交规而改变他已经构成的交通肇事罪的事实,更不能因为他以后不会违反交通规则,就认为他之前主观上也没有违反交通规则的故意。而前面的观点所提到的合规考察模式,实际上不就是从企业犯罪后没有了主观故意去推出企业在犯罪时也没有主观故意吗?这种推理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而笔者更想说的是,非系统性单位犯罪这一概念或者现象也许本来就不存在。我们都知道,如果要认定单位犯罪,必须要具备两个要素:一是能够体现单位意志;二是为了单位利益而实施。与非系统性单位犯罪关联最紧密的,是第一个要素,即单位意志。
《刑事审判参考》第305号案例(马汝方等贷款诈骗、违法发放贷款案)指出:“不同的单位针对不同的具体事项,决策机关和决策程序各不相同。或由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决定,或由领导层(董事会、理事会、厂委会)讨论决定、或由单位全体成员(股东大会、职工代表大会等)讨论决定,经过这些程序后单位成员的意志转化而形成了单位意志。经过这些程序形成的单位意志已是一种整体意志,完全不同于单位成员的个人意志。”
更为重要的是,单位犯罪中的单位意志,指的是单位犯罪意志,而不是一般的单位意志。很多时候,单位对具体的事项有单纯的意志,但实施、执行单纯单位意志的自然人很可能产生独立的犯罪意志,这种犯意超越了单位原本的意志,单位不应为此承担刑事责任。根据《刑事审判参考》第726号案例(周敏合同诈骗案),“公司的人格只有在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中才存在,如果滥用公司形式,违背公司的根本利益或者超出法定权限、程序,则股东的行为意志就与公司的意志相背离,公司就失去了独立的意志,而与自然人的意志混同,这种情形下显然只需要处罚自然人。
实际上,从实体法的角度看,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还是泾渭分明的,之所以实践当中存在争议,是因为单位意志和个人意志是否统一,在证据上并不太好明确。其实,无论是上文提到的英国的《反贿赂法》还是西班牙《刑法典》,都是一种法律推定,即根据经验法则,将举证责任转移给单位,如果单位无法举证证明具备完善的合规体系,就推定个人意志代表了单位意志,进而应当成立单位犯罪。既然如此,对于证据的采信、事实的认定,就应当是确定的,而不能通过案发后的行为去反推案发时的主观要素。
所以,如果从合规不起诉的角度来看,其正当性就不能再基于非系统性单位犯罪的责任较小进行论证了。因为从实体法的角度看,这些单位本身就不应该构成犯罪。

